四合院:开局投奔大伯,禽兽受死(金币大王)高分小说推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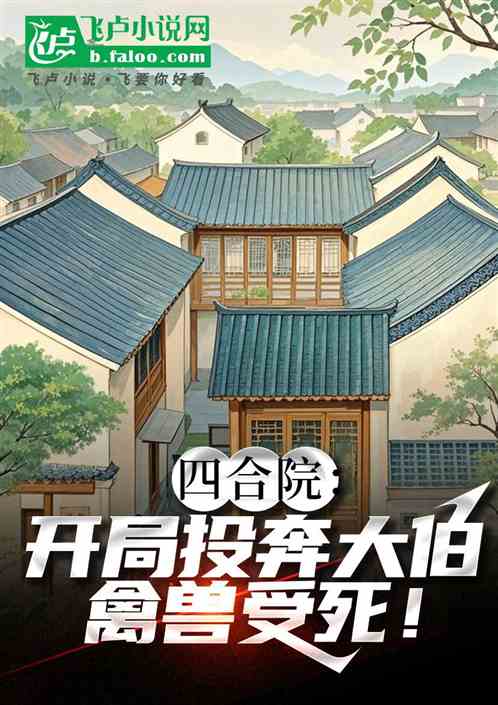
土木工程师张弛,意外穿越到了1959年的四合院。
两世坎坷,无尽疲惫,在他绝望之际,一个冰冷的机械音响起:
“恭喜宿主**号系统已加载完成,是否确认开启?”
系统能够让他通过接触他人拾取各种属性点!
“厨艺1”
“体质3”
……
随着属性的不断提升,张弛不仅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的增强,还逐渐展现出了过人的厨艺天赋。
在峨眉酒家,他从一名普通的切墩小工,一步步成长为五级厨师!
然而,易中海、刘海中、闫埠贵三位大爷各自为政,院子里的大小事务都充满了勾心斗角。
张弛初来乍到,便卷入了这些纷争之中……
推书试读:第1章
1959年的盛夏,阳光似火,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四九城的大街小巷,漫天的风沙像是一层朦胧的纱幕,让眼前的一切都蒙上了灰蒙蒙的色调,路上行人寥寥,个个都行色匆匆,躲避着那灼人的日光与恼人的风沙。
张弛,这个背负着两世坎坷的年轻人,正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包裹,行走在进城的土路上。
他本是后世一名整日与钢筋混凝土为伴的土木工程师,熬夜盯着打灰作业,谁想刚下到模板处查看,意外突如其来,垮塌的瞬间,世界天旋地转,再一睁眼,已然置身于这战火纷飞的年代。
此生开局,亦是满是凄风苦雨。
父亲奔赴战场抗击日寇,打小日子去了,却从此音信全无,徒留年幼的他与母亲相依为命。
母亲一介柔弱女子,靠着日夜操劳,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大,可岁月与生活的重担太过沉重,两年前,积劳成疾的母亲还是离他而去。
好在,还有大伯张大军时不时寄些钱来,加上邻里乡亲的照拂,日子虽艰难,却也磕磕绊绊地过着。
好不容易盼到初中毕业,刚满十七岁的他,竟在睡梦中莫名穿越,命运这双手,像是无情地捉弄,又似别有安排。
还没等他从这荒诞又离奇的穿越中缓过神,村子里公社的人就寻上门来。
原来,大伯因病骤然离世,身旁无儿无女,作为血缘至亲,张弛得进城去料理大伯的身后事,处理那些繁杂琐碎的财产安排。
一路上,张弛满心无奈,嘴里嘟囔着:
“上辈子打灰打出个好歹,这辈子也没个消停,我的那些个好日子哟。”
“8号、66号、88号,白冲卡了,那木工班组干活太糙,内撑都搭不明白,公司能赔几个钱,赔了又有啥用,这下全没了……”
顶着烈日与风沙,张弛走走停停,费了好大一番周折,终于寻到了南锣鼓巷95号。
望着眼前这古朴的四合院,他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熟悉感,正欲抬腿迈进,却见门里走出个干瘦老头,身着一袭灰色布衫,虽打着好些补丁,可浆洗得干干净净,透着几分利落劲儿。
老头抬眼瞧见张弛,镜片后的双目瞬间满是戒备,高声问道:
“你是谁,到我们大院来干啥?”
彼时敌特活动猖獗,进出城都得有证明,院子里也专门设有大爷负责安保看护,这老头便是三大爷闫埠贵。
张弛赶忙停下脚步,脸上堆起笑,客客气气地回道:
“大爷,我是张大军的侄子,叫张弛,张弛有度的张弛,来处理我大伯去世的事儿,这是我的证明。”
说着,便双手递上公社开具的证明材料。
闫埠贵接过证明,透过那副老花镜,上上下下打量着张弛手里的包裹,目光里透着审视。
张弛瞧在眼里,灵机一动,顺口夸道:
“哟,大爷,瞧您这通身的气派,一瞅就是肚里有墨水、有文化的人呐,怪不得能在这院子里当大爷,管事儿呢。”
闫埠贵一听,嘴角不自觉地上扬,心里头那股子得意劲儿就像春日里的野草,蹭蹭往上冒,心想着,这乡下小子还挺有眼力见儿,城里人见了我,怕更是得高看一眼咯。
当下也不摆谱了,转身往里走,扬了扬手,语气里还带着几分傲娇:
“进来吧。”
张弛心里直冒黑线,无奈地跟在后面,一边走一边在脑海里搜刮着记忆,试图回忆起关于这四合院的剧情,可绞尽脑汁,也只模糊记得几个人物好坏,具体事儿却是一团乱麻。
“罢了罢了,想不起来就不想,我一来,这剧情保准得大变样。”
他暗自嘟囔着。
没走多远,在前院一处屋子前,闫埠贵停下脚步,指了指屋子说:
“呐,就是这间屋子和旁边那小隔间归你了,你先收拾着,我去叫下一二大爷,咱一起陪你去街道办把事儿办了。”
说罢,也不等张弛回应,便大步流星地走了。
张弛撇撇嘴,进了屋子。
屋里空间宽敞,约莫有五十来平方,陈设简单得很,一张硬板床,一张四方饭桌,配着两个凳子,角落里立着个旧衣柜,瞧着有些年头了。
转头看向隔间,二十来平方的地儿,堆满杂物,还摆着个灶台。
张弛放下包裹,像个好奇宝宝,这儿摸摸,那儿敲敲,整日与混凝土建筑打交道,这木制的四合院结构对他而言,新奇得很,一会儿研究立柱,一会儿端详窗子上的雕花,恨不得趴地上瞅瞅地砖的纹路。
不多时,就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,闫埠贵领着两个人快步走来,一个是四十来岁、留着寸头的精壮汉子,另一个则是大腹便便、走路自带几分官威的中年男子。
还没到跟前,闫埠贵就窜到前面,介绍道:
“来来来,小驰啊,这是我们院的一大爷易中海,这是二大爷刘海中,两位大爷可都是院里的顶梁柱呐。”
又指了指张弛,
“这就是张大军的侄子张弛,是个懂事的好孩子。”
说罢,眼巴巴地看着张弛,似是期待着他再说出些夸赞的话来。
张弛这回可不敢乱夸了,赶忙向两位大爷问好:
“一大爷、二大爷好,我大伯是张大军,往后还请多多关照,叫我张弛就行。”
易中海目光深邃,上下打量着张弛,微微点头,嘴里说道:
“小驰啊,你节哀,你大伯在厂子里突然发病,送医院也没救回来,太突然了,咱们这就先去街道办,把手续和证明都办好咯。”
刘海中背着手,像个大领导视察工作似的,一脸严肃地接话道:
“老张同志一辈子兢兢业业,为厂子、为大家奉献不少,鞠躬尽瘁呐,你也别太难过,事儿咱一步步办好。”
张弛眼眶泛红,揉了揉眼睛,哽咽着说:
“谢谢三位大爷帮忙,也感激你们平日里对我大伯的照顾,这份情我记下了。”
这话一出,三位大爷却微微红了脸,他们心里清楚,之前以为老张是孤家寡人,平日里碰面,招呼都没打过几回,哪谈得上照顾。
一行四人出了四合院,往街道办走去,路上张弛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讲了些自己过往的经历,当然,土木那摊子专业事儿说了也白说,只提了提自己初中毕业的文凭。
三位大爷也七嘴八舌地说着院里的家长里短,只是奇怪的是,聊了半天,都没提到那个在张弛模糊记忆里被捧得颇高、与易中海关系匪浅的聋老太太,张弛虽疑惑,却也没多问,寻思着往后日子长,总会碰上的。
到了街道办,王主任早已等候多时,瞧见张弛,眼前一亮,这小伙看着虽瘦,可浑身透着股子机灵劲儿,皮肤黝黑,双目炯炯有神。
王主任清了清嗓子,说道:
“你就是张大军的侄子张弛啊,你大伯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,你也别太伤心,轧钢厂已经在处理后事了,我们街道办也和厂子沟通过工作名额的事儿,现在跟你说下安排。”
张弛收了收眼泪,认真听着。
“因为不是工伤,赔付这块儿会少些,只有200元。”
“不过呢,我们街道办会和轧钢厂一起帮你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,你大伯的工位也能继承,只是得等到你满十八岁,还有一年时间,你看咋样?”
王主任说完,搓了搓手,看着张弛,眼里满是期待。
张弛心里却另有盘算,他深知轧钢厂水深复杂,往后几年怕还有变数,自己这穿越而来,两眼一抹黑,又没个系统金手指傍身,贸然扎进去,怕是要惹一身麻烦。
于是,他带着哭腔说道:
“王主任,我和大伯相依为命多年,感情深呐,实在没法去轧钢厂,怕触景生情,心里受不了,您看能不能给我换个工作岗位,差点也行,我都愿意。”
王主任听了,眉头微微皱起,沉思片刻,说道:
“这样吧,我们街道在峨眉酒家有个后厨岗位,虽说比不上轧钢厂风光,可那也是四九城顶好的饭店,做川菜一绝,我都没舍得去吃上几回。”
“而且对年龄要求没那么严,你现在就能去,你觉得咋样?”
张弛一听,心里琢磨着,这峨眉酒家虽说比不上后世那些大饭店,可在当下,三年自然灾害刚开始,能在馆子后厨干活,起码不愁吃,顿顿能填饱肚子。
当下便点头应道:
“谢谢王主任,我愿意去峨眉酒家。”
王主任面露喜色,转身在抽屉里翻找一番,拿出个小簿子递过来:
“既然定了,那你就去峨眉酒家吧,这是你的粮簿,千万收好咯,在城里可不像农村,一日三餐都指着它呢。”
说罢,又看了看旁边的三位大爷,叮嘱道:
“95号大院一直是模范大院,你们三位也是院里的主心骨,小驰刚进城,往后有啥困难,你们多帮衬着点,要是再有难处,就来街道办找我。”
四人应了声,便离开了街道办,回了四合院。
到了院里,刘海中背着手,一副大包大揽的模样:
“小驰啊,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,我管着后院,事儿都能给你办妥咯。”
闫埠贵一听,急了眼,赶忙抢话道:
“你一大爷管中院,二大爷管后院,你在前院,归我管,有事儿找我就行,我就住你对门,喊一嗓子我就来。”
易中海看着两人争来抢去,淡淡一笑:
“都别争了,咱们都是一个院子的,小驰啊,要是晚上不开火,就来我家吃,大家互帮互助,别老想着管事儿,得真心帮衬着点。”
张弛心里直乐,脸上却摆出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:
“二大爷、三大爷说的都对,一大爷好意我心领了,谢谢各位大爷,现在时间还早,我收拾收拾,能开火做饭,就不麻烦大家了。”
三位大爷见状,也不再多说,各自回屋去了。
张弛回到屋里,打了盆水,里里外外忙活起来,把屋子拾掇得干干净净。
很快,天色渐暗,到了五六点钟,院子里渐渐热闹起来,各家各户炊烟袅袅。
张弛没出去凑这份热闹,坐在屋里,清点着大伯留下来的遗产,一共一百三十四元,还有一小堆粮油米面的票据,虽说不多,可在这年月,也是笔不小的财富了。
收拾完,张弛起身进了厨房,端出蒸好的棒子面窝窝头,配上一小碟咸菜,坐在桌前,大口吃起来,可这窝窝头又糙又喇嗓子,吃得他直皱眉,心里直嘀咕:
“这日子可真难熬,吃不好,睡不好,没空调吹,还净是事儿,这窝窝头哪比得上后世的杂粮饼哟,也不知道往后日子咋过,明天得出去熟悉熟悉这四九城,找找活路。”
与此同时,中院的易中海家里,饭菜虽简单,只有两个素菜,可他却破例倒了杯酒,慢慢品着。
一大妈收拾完厨房,瞧见他这模样,不禁问道:
“中海,你今天咋了,咋一个人喝上酒了?”
易中海是七级钳工,平日里为了干活,酒都很少沾,逢年过节才会抿上几口,今儿这般,着实反常。
他盯着酒杯,叹了口气:
“今天见着老张那侄子了,是个机灵孩子,之前以为老张孤苦伶仃,没个亲人。”
“想着以后我俩还能有个照应,谁想他这一走,倒有个侄子来摔瓦挂幡、上香,咱以后咋办呐?咱家东旭,能指望得上吗?”
一大妈眼眶泛红,自责道:
“都怪我,吃了那么多药,也没能给你生个一儿半女,要不咱收养个孩子吧,东旭虽说有媳妇孩子,可他那性子,能孝顺咱吗?”
易中海摇摇头,苦笑道:
“收养孩子哪那么简单,从小养大,谁知道孝不孝顺,有没有本事,东旭虽说只是个二级工,好歹也有四十多块工资,媳妇也贤惠,把他妈照顾得挺好。”
“咱这养老,还真没个准谱儿。”
一大妈张了张嘴,欲言又止,屋里一时陷入沉默,只有易中海那轻轻的叹息声,在昏暗的灯光下,悠悠飘散,似是对未来的迷茫,又似对生活无奈的妥协。


